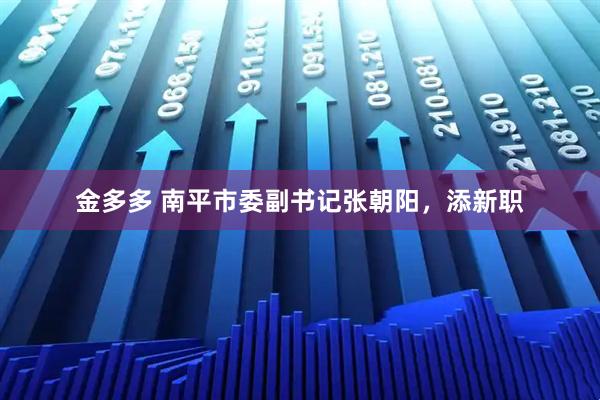父亲识得山珍,尤其对野生菌了如指掌。每年进入雨季涵星配资,几场大雨过后,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尽,父亲便背起背篓钻进了树林。他总说,这时候是找野生菌的最佳时期,菌子藏在腐叶底下,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。
一大早,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像接到某种神秘指令,背起背篓出门,三个小时后准能带回满篓的惊喜。
每年的青头菌是最先登场的。它们躲在松针铺就的软毯下,菌盖颜色为浅绿色或灰色,菌肉白色,味道柔和,无特殊气味,炒吃味鲜美,菌柄圆柱形。父亲教我辨认菌子:“看菌褶,清白无杂色的才是好东西。”他采菌子从不用蛮力,拇指抵住菌柄底部轻轻一旋,整朵菌子便带着松木香落进篓里。记得小时候,我和父亲上山捡菌子,我贪多,把菌帽缘发褐的青头菌也捡了,他立马挑出来:“这是被虫啃过的,吃不得。”听父亲说,我老家山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捡菌子。不光我们的村民,周末还有不少城里人来捡。
鸡油菌要到深秋日头足的时候才肯露面。橙黄的菌盖像朵迷你小喇叭,丛丛簇簇躲在蕨类植物底下。父亲说这菌子“认时辰”涵星配资,得趁露水没干时采,不然香味要跑掉一半。他总在鸡油菌最丰茂的那片坡地留个记号,来年再去,准能在老地方找到新菌。采回来的鸡油菌易清洗,只用软毛刷轻轻扫去浮尘,和腊肉同炒,油汁浸得菌子透亮,满屋都是暖融融的菌子香。
展开剩余58%最惊险的是碰上山中毒菌。有一次我在松树下发现一朵颜色鲜艳的菌子,正想伸手去摘,父亲猛地拽住我手腕:“这是毒菌,不要拔!”他蹲下来,用树枝拨开菌子周围的土:“你看它菌柄上的环,还有底下的托,都是有毒的记号。”说着从兜里掏出前不久政府发放的预防野生菌中毒宣传画,让我认识菌子,可见他对待菌子中毒是认真的。
有一年我从部队探亲休假回家,父亲背着背篓在山里转了一上午,带回十几朵鸡枞菌。他把鸡枞菌撕成小块,和土鸡同炖,洁白的汤面上浮着一层浅黄的油花。“这东西很补的,是难得的山珍,很难找到。”他往我碗里舀汤,“你在外地吃不着,难得回来要多吃点。”那汤鲜得舌头都要化掉,我喝着喝着,眼泪就掉进了碗里。
2018年我回到老家县城工作,每到阴雨连绵时节我都会收到父亲送来的菌子。每次父亲送来菌子,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,父亲每次送来菌子都会来上一句,“菌子一定要煮熟煮透,不然会中毒”,说完就匆匆赶回老家。妻子把菌子清洗干净,待油烧至冒烟时,野生菌倒进铁锅,“滋啦”一声腾起白雾,混着蒜香弥漫满整个屋子,这是山珍,更是人间美味。
如今,父亲已经离我们远去,老家的背篓也挂在墙上生了锈。但每次吃野生菌,我总会想起他蹲在松树下采菌子的模样,想起他给我交代煮菌子注意事项的表情。那些藏在菌子里的时光,混着草木香和父爱的温度,成了我味蕾深处最珍贵的怀念。
前不久我公休假,连续去山上转悠了三个早上,只收获三朵没人要的红菌子,顿时让我心灰意冷,虽然我不是找菌子的“料”,但我会怀念父亲找的野生菌,我想,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骨子里,像野生菌的菌丝,在岁月里悄悄蔓延,牵出一整个温暖的秋天。
作者:张芹洪(作者单位系牟定县委宣传部)
转载请注明来源《民族时报》涵星配资
发布于:云南省恒汇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